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不断的发展,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性质和规模,使作战样式、作战方法、作战环境、作战条件等诸要素已较以往发生了诸多变化,未来战场变得更模糊不清,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战争在规模和层次上,可划分为战略、战役和战术,在以往战争中三者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从三者相互关系上,战略决定战役,战役决定战术,而且战术反作用于战役,战役又反作用于战略,这是战争本身存在的内在规律。随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技术战争发展为信息化战争,虽然未从根本上改变战略、战役、战术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但是却使战略、战役、战术行动规模的日益模糊。这是因为,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目的、规模和使用兵力、兵器有限,战争维持的时间短,政治性突出,战争与战略、战役、战术结合得十分紧密,趋于一体。信息化武器和兵器打击精度高、威力大、射程远,具有全天候、全时空的平战结合的侦察与打击一体化能力,为迅速达成战争目的提供了有效手段,有时不动用大部队也能达成战略、战役目标。任何一个作战单元,甚至是单兵的战斗行动,都能得到强大的信息和火力支援。在它们的作用下,战术打击可以直接达成战略目的,战略指挥可以每时每刻介入战术层次已不再是梦想。由此可见,以往通过局部小胜逐步汇集成战略性胜利的作战理论受到冲击,战略、战役、战术三个作战层次间的界线日益模糊。
随着大量使用精确打击兵器、隐形兵器、无人机,因而通过一、二次火力突击就可达成战役或战略目标。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首先是通过大规模的战略空袭行动,尔后通过地面诸军种联合作战达成了战争目的;美军入侵巴拿马,是通过动用陆军实施五路重心攻击的战役行动达成了预期目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军主要是通过空中精确打击和特种部队搜剿达成了战争目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空中打击掩护下,美国陆军师通过战术行动达成了战争目的。作战规模、层次的模糊性,是信息战本质特征的反映。在信息战中,敌对双方为迅速达成既定的战略目的,将会超常使用作战力量,最大限度地投入先进的技术兵器和精锐部队,力求在极短的时间内摧毁对方的指挥控制管理系统,以夺取战场上制信息权的优势。信息战的这一特点,使战役战斗与战略目的无显著的区分,作战规模也没明确的战役战斗的区别。一次战役既可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一次战斗也可能实现战争的目的,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战役战斗的战略作用。特别是各种精确制导武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侦察监视系统、隐形武器、C4ISR系统等信息化兵器的广泛运用和快速反应部队、特种部队、战略预备队等频繁投入战场,使得作战规模的界定模糊性更加突出。
因此,在未来信息作战中,作战双方都将以不确定的作战规模,采取超视距精确打击、非程式化“点穴”和结构破坏等战法,打击对方的战场感知系统与信息系统,以便迅速地达成作战目的。这样,战场上的特种作战部队就可能大显身手,即在战前秘密地深入敌后,直接攻击和瘫痪敌指挥控制管理系统,使敌失去对其作战力量的控制,从而陷入指挥混乱、协调无序的困境。这种规模的作战虽然较小,但对于作战的胜负却能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技术决定战术,同样也决定着军队的编制体制和军兵种构成。例如,火炮、化学武器、无线电报机等武器装备的出现,为炮兵、防化兵、通信兵等新兵种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就军种而言,由于飞机的出现,进而产生了空军;船舶的问世,催生出了海军。工业时代,要求的是分工合作,所以细化和产生的专业慢慢的变多,体现在军队的构成上,就是军兵种划分得越来越细;信息时代,要求的是整体作战,各专业之间密切协同,走集成一体化联合作战之路。反映在军队的构成趋势上,就是作战系统的一体化。比如,未来许多武器装备系统将形成一个独立的作战单元,既可完成陆军要求的作战任务,也可实现空军的作战要求,还可达到海军的作战目的。换句话说,当未来作战飞机的续航能力无限延长,并超越大气层作战;陆军告别“地面爬行”,实现全球抵达、全球作战;海军实现由海到陆、到空的作战能力转化之时,一体化作战必然催生一体化部队。一体化作战部队,一般由装甲兵、炮兵、机械化步兵、导弹、攻击和运输直升机、海军舰艇等组成,能独立作战,将实现专业军队向职业化军队过渡。
未来一体化部队将主要体现为,将打破传统的陆、海、空、天等军种体制,按照系统集成的要求,建立“超联合”的一体化作战部队。未来信息化战争是高度一体化联合作战,使用传统的诸军种力量实施联合作战,已难以适应这种高度一体化联合作战的需要。为此,未来军队组织的编成,将打破传统的陆、海、空、天等军种体制,按照侦察监视、指挥控制、精确打击和支援保障四大作战职能,建成四个子系统,即:探测预警子系统、指挥控制子系统、精确打击与作战子系统和支援保障子系统。这四个子系统的功能紧密衔接,有机联系,构成一个相互依存庞大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系统。按照这一个思路构建的军队,将从根本上抛弃工业化时代军队建设的模式,革除偏重发挥军种专长和追求单一军种利益的弊端,使作战力量形成“系统的系统”或“系统的集成”,从而能够充分的发挥整体威力,实施真正意义上“超联合”的一体化联合作战。
军兵种作战力量具有不一样的打击目标和执行不同作战任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力量主要以步兵为主,绝大多数都是步兵与步兵的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武器装备的发展,飞机、坦克、大炮用于战争,军兵种之间的作战任务有了明显区分,通常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但是在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由于武器装备向多功能一体化方向上发展,部队的编制内,不仅有各兵种,还有各军种。作战部队既能执行地面作战任务,又能执行打击空中和海上目标任务,使军种间作战的界线将不易区分。例如:摧毁敌方坦克的兵器,可能是已方陆军的坦克或反坦克兵器,也可能是空军的飞机或海军潜艇发射的“智能”型导弹。美军计划组建四种一体化部队:由装甲兵、炮兵、导弹兵、攻击与运输直升机组成的一体化地面部队:编有“飞行坦克”的陆空机械化部队;由多机种组成的空军混编联队和中队;由各军种部队组成的“联合特遣部队”。俄军拟组建集各军兵种于一体的“多用途机动部队”,由地面、空中和太空兵力组成的“航空航天部队”,以及由各军种非战略核力量组成的“非核战略威慑部队”。
在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中,武器装备向多功能、一体化方向发展,部队的编制趋向混合化、小型化。作战中,各军兵种围绕既定的作战目标,彼此依存,融为有机的整体。在战场上,各军兵种将在陆、海、空、天、电等多维领域,围绕统一的作战目的,既在活动空间上相对独立,又在作战行动上高度融合,使得不同军兵种所执行的任务界线变得更模糊。

传统战争的动因一般是政治斗争掩盖下的经济利益之争。在信息时代,经济利益之争仍将是导致战争的最终的原因,但除此之外,由于各国之间、国际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交往增多,联系密切,这就必然导致各个国家、民族、社团之间由政治、外交、精神等因素引发的冲突增多,使宗教、民族矛盾上升,使暴力活动、走私贩毒、恐怖活动国际化。这些矛盾与冲突不仅是“亚战争行动”的直接根源,也是导致战争的动因之一。1991年海湾战争直接动因,是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通过了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拉克无条件从科撤军。美国出于保护西方石油来源和为建立符合其利益的世界新秩序的目的,乘虚而入带头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名,出兵海湾。通过42天的交战,美军达到了战争目的。伊拉克战争,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而发动的一场非正义战争。整个战争中,美军作战的重心是针对萨达姆等少数伊拉克高层领导人,并以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展开的攻击行动。虽然战争已经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是美国至今仍然没找到伊拉克拥有这种违禁武器的有力证据。在这场战争军事目的上,美国也还是为了试验新的作战理论。
近几年,美军大力倡导军事变革。指导伊拉克战争的理论是“网络中心战”理论,并运用1996年提出的“震撼与威慑”的新理论:强调运用猛烈的火力,震撼性打击对手,不分前沿和纵深,全方位迅速地对敌人进行打击,运用先进的精确制导技术,打击对方目标时片面追求双方较少的伤亡;空中与地面行动同时展开,目的是摧毁对方的意志,使其政权崩溃,进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不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而是利用高技术加特种兵的战术进行作战,这是美军军事变革的主要成果之一。
以往攻防作战的程序十分明,进攻一方通常按照进攻准备、突破、冲击、纵深作战等步步进攻程序进行,防御一方按照防御准备、火力反准备、反冲击、纵深抗击等分段抗击作战程序进行,攻防双方各个作战阶段展开有序。而高技术武器装备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军事革命将改变未来作战程序,作战行动将突破固定的战场和阵地的限制,在整个作战空间的各个层次、各个方向、每个方面一起进行。这样一来,以往战争中的前后方界线模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正面和固定的战场不复存在,进攻行动和防御行动的界线因为战场的高度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也变得模糊不清并影响世界军事力量平衡。攻防兼备、攻防一体作战尤其是攻防一体的信息战将成为今后作战艺术的焦点,使每一次战争都有攻中有防、防中有攻。
攻防作战将在陆、海、空、天、电以及外层空间和前沿与纵深、正面与翼侧、前方与后方同时展开,战场机动频繁,线式作战样式已不适应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发展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非线式作战,形成一种“岛屿式作战基点”,前方与后方的界线、敌我双方的战线变得模糊,战场呈现流动的非线性或无战线状态的多维立体战场。
以往衡量一场战争胜负的标准通常指的是歼灭对方多少兵力,缴获多少武器,占领多少城镇和领土,然而在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衡量一场战争胜负的标准已不只是这些。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政治目的与战争结合得紧密,战争企图往往不通过侵入对方领土,全歼敌军或使敌方彻底投降,以免引发世界舆论的和民众的强烈反对,造成政治上的被动。
信息化战争的一大特点是,将使伤亡、破坏,特别是附带性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通常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精确打击,避免重兵集结进行面对面的拼杀,打一场像美军惩罚利比亚发动的“外科手术式”作战,实施空中远程机动空袭,达成战争目的;也可实施导弹,进行远隔千里的攻城战,也能达成局部战争的目的;也可像海湾战争那样,不占领其国土,不杀伤其一兵一卒,不缴获其武器、弹药,实施的大规模的空袭战,削弱其军事设施,捣毁其国政权。
以往的战争,由于受信息基础设施和技术的限制,军队与社会的联系相对“松散”;纯战争的武器装备亦导致完全独立于民间之外的军事组织。信息时代,信息成为军民结合的纽带,这种结合,跟着社会和军队的信息化程度的发展,融合程度也将逐步的提升。这就使得社会和普通民众不再是战争的旁观者,甚至也不仅处于支援和从属地位,而是与军队一样,从战争的幕后走向了前台。
正如人们看到的,一方面,现代战争的目的已不再单纯地追求攻城掠地和最大限度地歼灭敌有生力量,打击目标亦不再局限于敌方的重兵集团和军事设施,而是包括对应赖以生存和运转的基础设施,如:金融网、电力网、交通网、行政网、通信网等。另一方面,战争有向“平民化”发展的趋势。比如,信息化使得“非国家主体”具备了与国家力量进行对抗的能力。任何一个“非国家主体”,只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和信息设备,就可以对一个国家的要害目标进行攻击,其危害有时并不亚于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比如基地组织对美发动的9·11袭击,就是如此。信息战力量的构成,虽然仍具有以往战争全民参战的痕迹,但是在构成的形式和作战的质量上,由于较多地加入了信息化的含量,特别是较多地加入了全社会民众的信息战能力,所以无疑使判断信息战具体参与力量时的思维趋于模糊,而为作战决策与指挥带来较大的困难。随信息技术深入发展,社会民众的信息化程度也将极大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的信息战,就更突出军民兼容的特征。特别在信息战中,许多高技术工作,仅靠军队的力量难以独立完成,还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协作,这就使信息战的作战力量,较多地融入了全民皆兵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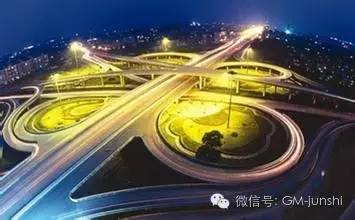
以往交战双方力量对比,通常以军队人员数量多少、各种武器多少的比数来衡量力量优势,进行筹划攻防作战。但在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集中兵力的内容和方式有所改变。力量的对比不只是考虑数量多少,更主要是考虑质量,尤其是要考虑集中火力和信息,各种远程打击兵器不需要集中部署,就可对目标实施集中突击。要使集中后的火力有效地发挥作用,还必须集中大量信息,否则就无法捕捉、跟踪和摧毁目标。军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武器将不再是高性能的战斗机、轰炸机、坦克、战舰,而是由信息系统涌现的巨大数据洪流。无形的信息和知识像装甲雄师一般,在作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并日益成为最重要的战斗力和力量倍增器。计算能力、通信能力、侦察能力、解决能力、决策能力、计算机模拟能力、网络战等信息和知识因素都将成为衡量军事力量的关键因素。
军事力量的对比,慢慢的变多地取决于信息武器系统的智力和结构力所带来的无形的、难以量化的巨大潜力。因此,以往根据作战人数和坦克、飞机、大炮、军舰等武器装备的性能、数量等静态指标评定军事力量强弱的方法显然受到了挑战。因为信息武器系统的智力、结构力具有巨大的动态潜力。海湾战争的兵力对比和战争结局就可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战前,伊拉克与多国部队的兵力对比是1.6:1,但战争结果是伊军的伤亡为多国部队的100倍。显然,若不是多国部队的大量信息武器系统发挥出成倍的作战潜力,是不会有如此战局。可见,静态数质量指标的力量评估原则将会被一种全新的力量理论所取代。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普遍的应用于未来战争,使现代战争信息量很大,处理信息已经十分困难。如: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平均每月要处理军事信息815000多份,差不多每天处理26500份。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在42 天作战中,处理军事信息多达数百万份。仅美国陆军后勤每天就要处理军事信息10700份。在军队、武器装备和战场都实现数字化以后,军事信息高速公路将覆盖整个作战空间,这一些信息有真有假、有新有旧、有重有轻、有虚有实、有粗有细等,信息像潮水般地向红蓝双方指挥所涌来。在这样快节奏、战机稍纵即逝、信息海量战场环境中,给红蓝双方指挥员短暂决策处理时间,逼着双方指挥员在错综复杂的战场信息中锻炼辨别力、分析判断力、快速决策力,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提高指挥能力。
战场是指敌对双方作战力量相互作用并加上作战力量机动和火力杀伤的最大距离。以往战争中,由于受武器装备水平的限制,冷兵器时代的战场空间,基本局限在交战双方的目视距离之内;热兵器和机械化战争时代,战场空间由火器的射程和双方兵力的机动能力所决定,并随着火器(炮)射程和兵力机动能力的逐步的提升,战场空间日渐扩大,并由单一的陆地战场,发展到海洋战场和空中战场;作战距离则由目视距离发展到远程和超远程,战场的纵深和维度不断拓展。进入信息化作战后,随着军队武器装备和结构的发展变化,现代战争的作战空间又从传统的陆、海、空向太空、计算机空间,特别是信息、心理、电磁、认知等虚拟空间拓展,加之现代武器装备的射程及机动能力大幅度提高,未来战场的前方和后方变得日渐模糊,除了在固态的地理空间上有前后之分外,在动态的行动空间上已无先后之别。战斗既可能从前方打响,也可能从纵深开始。特别是数字化部队的建立,使军队选择作战行动的方式,具备了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同时,也为准确地判断对方作战行动空间的具体范围和准确位置,增加了复杂度。一是信息化武器大幅度的提升了军队的远战能力,使军队的战场打击方式灵活性更好。二是信息化武器大大增强了军队的全时空、全方位快速机动能力,使信息战的交战区域更加扩大。
军事航天能力和远程空运能力的提高,武装直升机的广泛运用,为实现远距离快速机动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未来信息战,或在三维空间或在四维空间进行,一般不易准确把握。而只有当对方的作战行动达到一定规模时,才有机会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增加了指挥和控制的难度。作战空间的模糊性,还表现在作战行动范围的模糊。由于未来信息作战将打破由前沿向纵深逐次推进的格局,在多维的空间内进行全方位、全纵深的交战,就使作战行动的范围增大,作战空间变得难以捉摸。信息战所具有的作战行动规模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作战空间的多样性。这也使判断对方作战行动的空间,变得模糊起来,而呈现出不易预测和控制的特点。

先进的信息技术,不仅实现了侦察情报的实时化和战场数字化,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效能,更重要的是出现了许多崭新的作战手段:如以信息战的声势和威力使敌慑服的信息威慑;以分散、隐蔽和广开信息通道的办法来进行的信息屏蔽;对敌战场认识系统和信息系统实施的信息攻击;通过信息系统隐真示假行动的信息欺骗以及信息割断、计算机病毒袭击、特种作战、心理战、非接触作战、非致命攻击、结构破坏战等,这些作战手段运用于信息战,完全改变了以往攻防作战程序清晰、连贯性强的特点,使作战手段运用的非有序性、作战形式的非模式化等特点越来越突出,进而导致了在信息战中,对敌方作战手段运用的规律、时机和方法,变得更难以揣度。在手段组合上的模糊,即在作战过程中,因势因敌恰当地选择打击手段,并灵活地进行组合,使敌无法判断对方将要采取何种作战手段,无法有效地采取对应的保护措施。在运用时机上的模糊,即根据作战的意图和作战目的,针对不同的作战阶段和不同的作战领域,采取不同的打击手段,降低敌抵抗意志,使之陷入困境。在打击目标上的模糊,即利用信息战作战手段多样化的特点,针对信息作战的需要,既可声东击西,亦可声东击东,灵活地打击敌指挥中心、通信中心或雷达站、防空系统、后勤保障系统等关键节点,使敌难以对我作战手段的运用作出准确的预测。
上一篇: 浅谈俄军总参谋部体系
下一篇: 严为民:区别下战略和战术!这一信号


 服务热线:
服务热线: 


